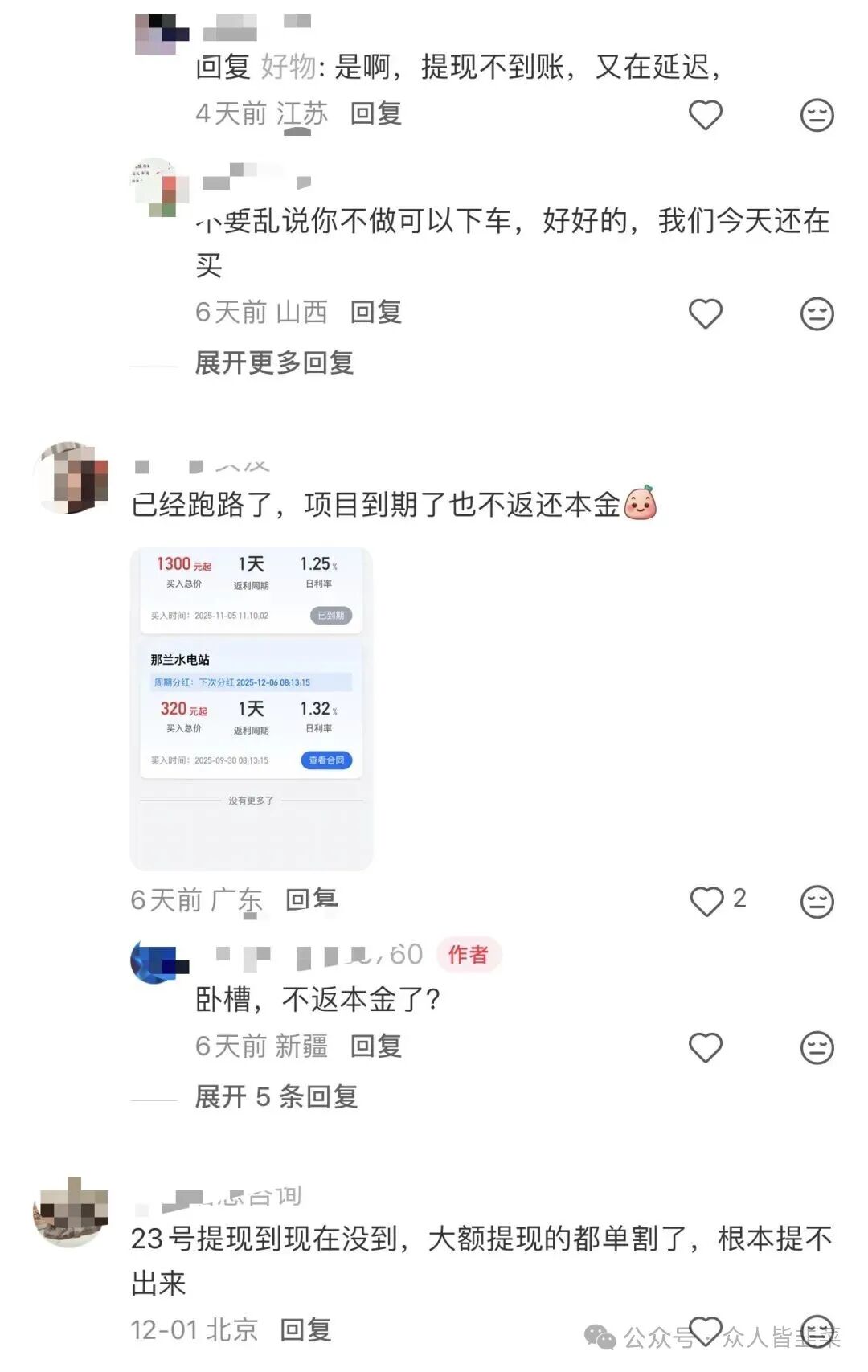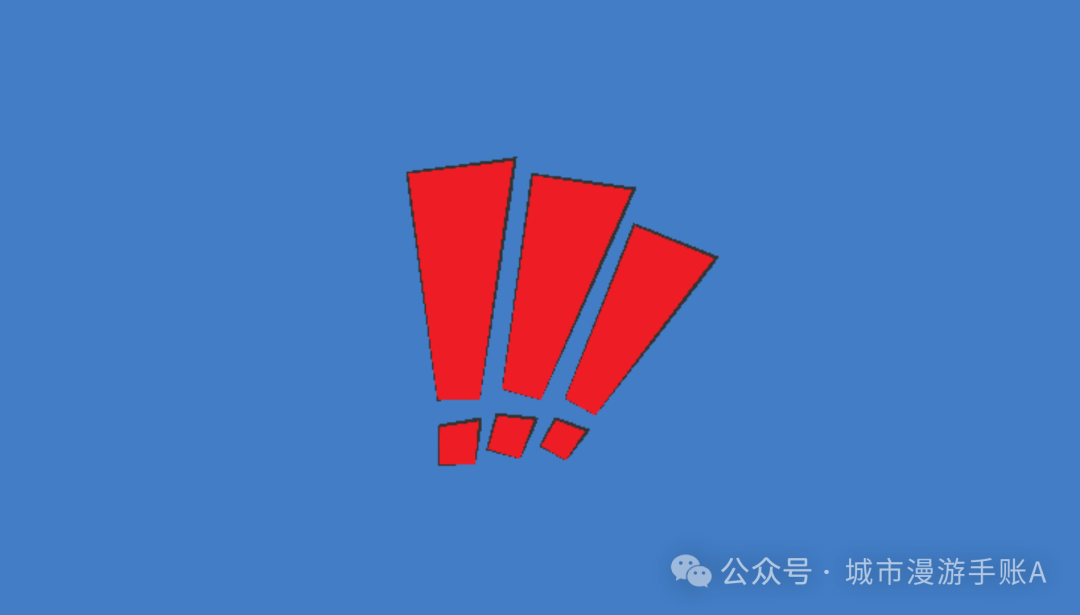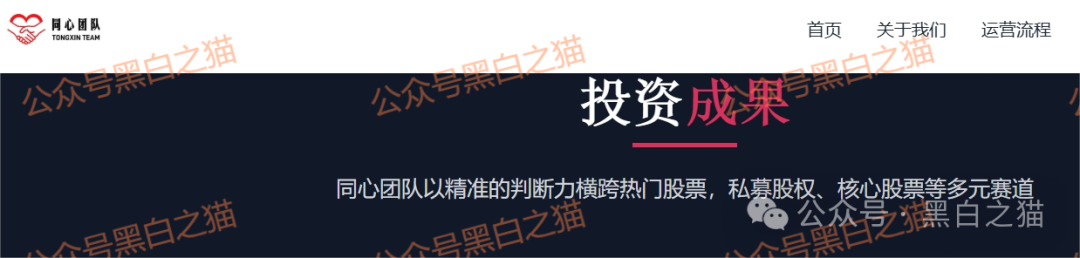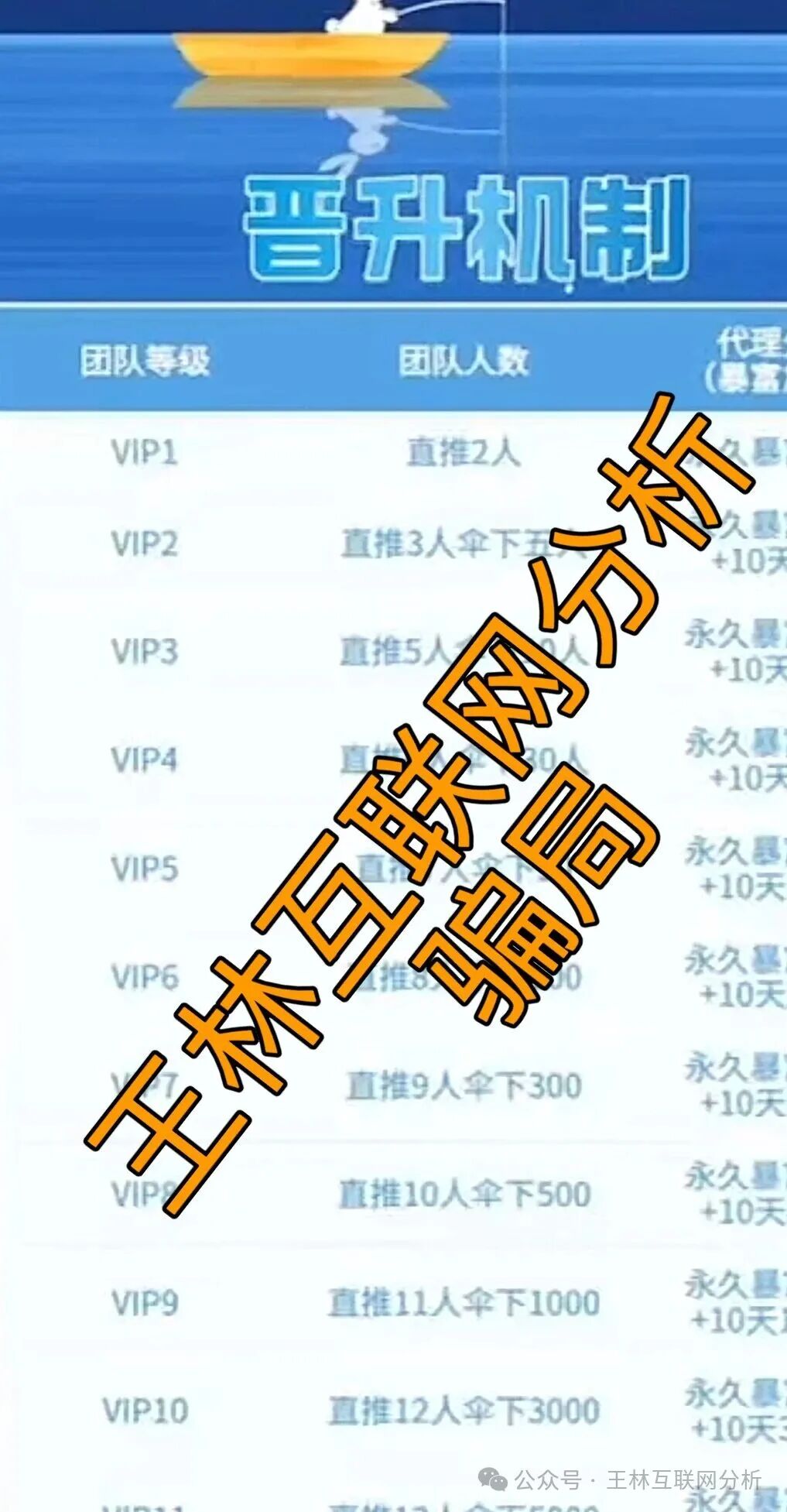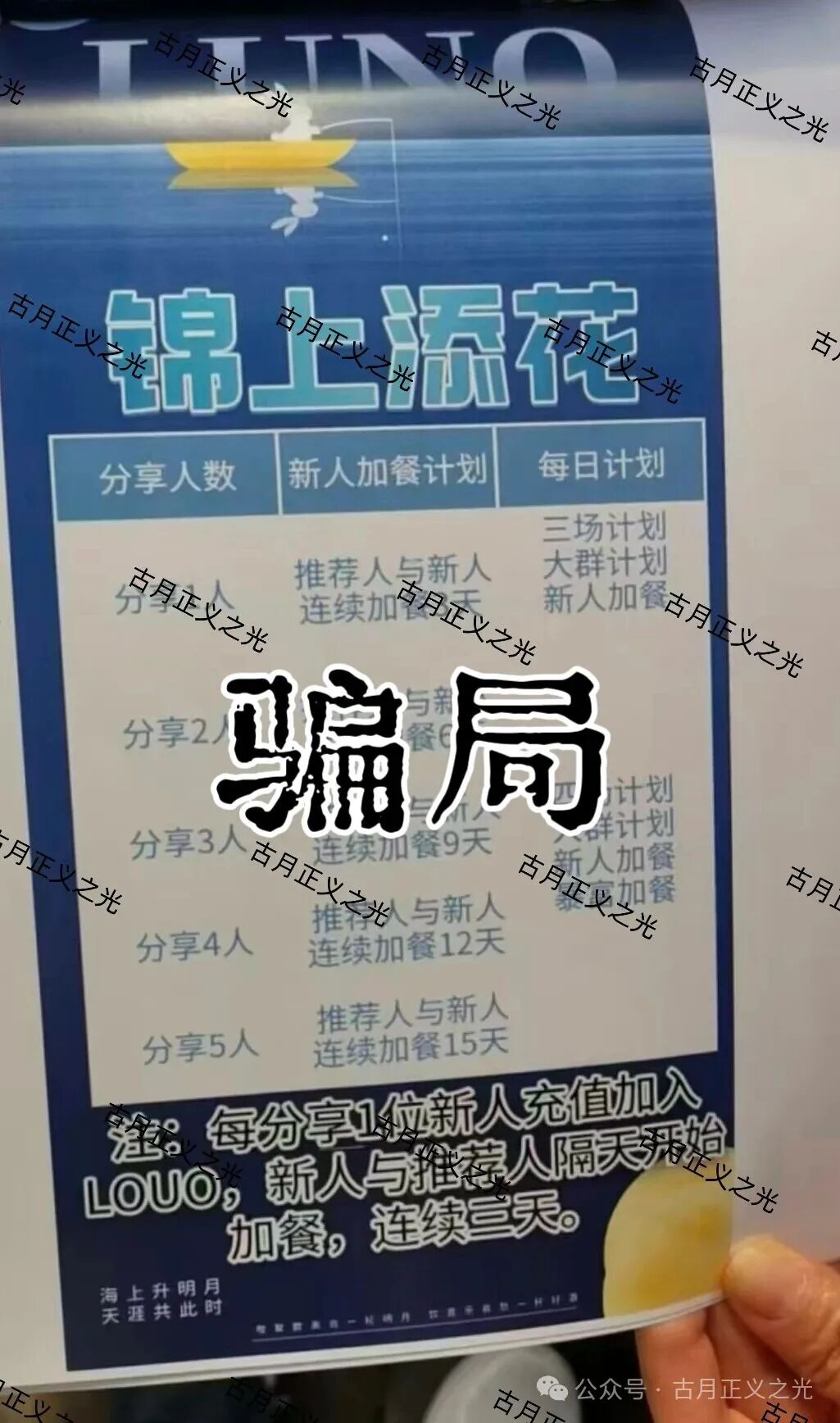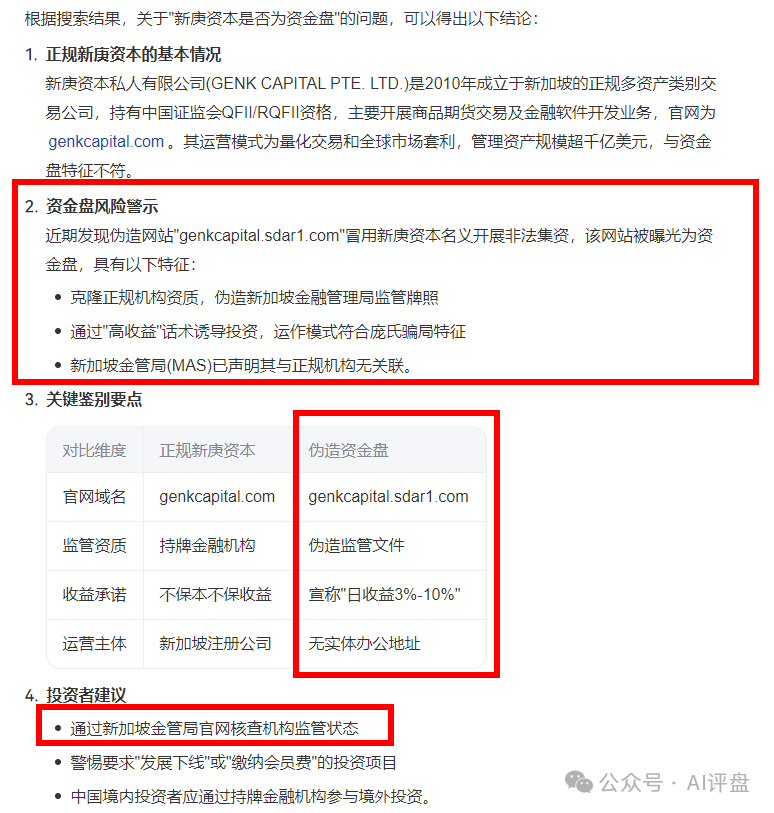农信社发展至今已70多年,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从未间断的金融机构。农信社既为我国“三农”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,又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种风险和困难。一路走来,农信社的定位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会不断地被提出来探讨,而核心问题聚焦于,农信社的发展目标是否清晰?定位是否明确?是做以服务“三农”和小微为宗旨的金融机构,还是一般意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?是“以服务为先”还是要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?上述一系列问题有待清晰。
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“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”,基于这一要求,结合农信社改革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,需要对农信社定位进行更深入地剖析,让农信社的DNA更加明确地展示出来。
既然要“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”,那么,源于农信社的先天基因与角色,就决定了其具有独特定位和特殊使命,农信社并不是一般意义的“商业银行”,与国有大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其特征表现为,根植县域,存有合作制属性,服务本地社会经济为先,做小做散,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,具备风险可控及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,积极融入社会治理,服务社区,做真正意义的支农支小主力军。
从体制机制角度来看,凡是坚持上述定位、使命和责任的农信机构,即使面临经营环境等诸多压力,其经营情况和发展韧性均是良好的,这从今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对189家优质机构开展的调研结果可见一斑。此次调研涉及农合机构162家,村镇银行27家。从区域看,这些机构分布在全国25个省(区、市),遍布东西南北,有的位于大中城市、发达地区,也有的地处经济相对滞后甚至艰苦边远的县域。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发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4年9月末,调研机构总资产17万亿元、各项贷款9.3万亿元。平均不良贷款率1.2%,拨备覆盖率343%,资本充足率15.2%。资产利润率、资本利润率分别为0.9%、11%。被调研机构以30%的资产规模,贡献了农村中小银行50%的净利润。
从上述调研结果来看,既不是农信机构的体制机制有问题,也不是其没有发展空间,而是农信机构是否能够坚守定位和使命,是否持续强化自身做小做散,服务“三农”和小微的能力,是否能够耐得住寂寞,控制“做大”的冲动,这一切正契合了是“以服务为先”还是要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的问题。要想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的答案,要先明确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和“商业可持续”是什么关系。
基于农信社的定位,需要构建其商业可持续能力,但商业可持续并不等于要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,这也是在全球合作金融发展的过程中,被充分验证的事实。一般意义的商业银行,其目标大多数会是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,“追求利益最大化”不一定就可以做到商业可持续。而合作金融本身被证明是相对稳定,且商业可持续能力较强的金融组织机制。在历次全球金融危机中,具有合作金融属性的组织机构的抵御风险能力较强,其金融健康度被认为优于纯商业金融主体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、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认为,尽管近些年来,之前的一些合作金融属性的主体也存在“越来越商业化”的倾向,但其与社区和“成员”的关联性依然较强。合作金融并不把盈利当作主要的目标,体现为比较稳健的经营方式,其波动比较平滑,经营主体自身风险免疫能力较强。他同时指出,小银行的优势是会做好平衡商业收益和服务的关系,增强社区客群的黏性,在提供非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的同时,解决好商业可持续的问题。
值得注意的是,商业可持续并不等于“股东可以赚到更多的钱”,这与股份制存在先天的“对立”,这也是合作金融本身的基因特征。参与合作金融运作主体的“股东”,大多并不是想通过“金融”赚钱,而是为了增加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。信用社最初的目的之一也是“为成员提供服务”,其非盈利特征是天然的。但既然大部分农信社已经走上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道路,那就要回归农信的本质,也必须遵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要“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”。
如果说农信社定位如此,那么,无论从监管端,还是从市场端,都不能把农信社作为一般的商业银行看待,也不应该让其走上一般的商业银行道路,这与中央对于金融工作的要求并不一致。与此同时,对于一个个农信机构而言,如何坚守定位,如何不忘初心,认知并践行使命与责任,这的确是在微观操作层面需要解决好的问题。结合金融监管总局农银司发表的文章《萃取优秀经验 办好农村中小银行》中所述的“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”内容来看: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坚持正确的业绩观和发展观,聚焦主责主业,下沉经营重心,把“扎根当地、深耕县域、做小做散”刻入农信基因,大力弘扬农信精神,不断延伸农村金融服务广度,拓展服务深度,提升服务温度,切实巩固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主力军地位。此番表达既解析了农信社的DNA,也全面诠释了农信社的定位,指明了农信社发展的方向。